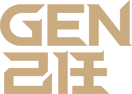《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自《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三款即已有此规定。而其渊源则可追溯至《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关于这一条规定的适当性似乎并没有太大争议,立法者也认为这一条与《合同法》第五十条实质上是相同的。然而问题可能并非如此简单,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究竟能否被限制,《公司法》第十六条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决策权限的规定究竟限制的是什么权力?《九民纪要》以及《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中关于代表权被限制时的第三人保护是否需要进一步分析?公司责任与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责任是何关系?相关问题其实均有待进一步分析。
一
对外“代表权”能否被限制
暂时不讨论《民法典》与《合同法》的规定是否实质相同,如果做一下比较法分析就会发现,关于公司代表权的限制问题,欧盟或者德国的公司法规定与我国大相径庭。比如,德国《股份法》第82条第1款明确规定,“董事会的代表权不得受到限制”,且没有规定任何例外情形。对于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法》第37条第2款规定,“对公司总经理的代表权的限制对第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这一条规定虽然原则上承认有限责任公司项下代表权可以被限制,但是对第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而不仅仅是对“善意”第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在欧盟公司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在2017年欧盟《关于公司法相关问题的指令》中,其第9条第2款就规定,“基于公司章程或公司有权机构的决议而对特定公司机构的权能进行限制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即使上述限制已经对外公开,亦不例外”。
为何制度安排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其实关键点就在于对“代表权”概念的界定上。
(一)被混同的对外"代表权”与对内"管理权”
在德语中,“代表权”(Vertretungsbefugnis)是指代表法人对外从事法律活动的一种权能,而对之相对应的是对内“管理权”(Geschäftsführungsbefugnis)。根据《股份法》第82条的规定,对内的管理权可以通过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公司内部规则等方式予以限制,但对外的代表权不能被限制。第82条第1款规定,“董事会的代表权不得受到限制”,第82条第2款则规定“涉及董事会成员与公司的关系,在股份有限公司的规范框架内,公司章程、监事会、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议事规则涉及的对管理权的限制,应当得到遵守”,上述规定即充分体现了二者的本质区别。
在我国公司法上,法定代表人这个概念也只在对外法律关系中才有意义,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是对外代表公司的一种权能,而不是对公司内部的管理权能。公司内部关系中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是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其与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其他机构之间不会在“法定代表人”层面上产生法律关系。
代表权与管理权确实存在紧密的关系,有的管理事项不涉及对外法律关系,因此不会与代表权产生重合,但有的管理权针对的事项直接涉及对外法律关系,因此如不加区分就容易被混同。比如,以我国公司法上被认为最为典型的法定代表人“代表权”受到限制的情形——公司对外担保为例。对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主体予以限制其实并不涉及限制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问题,而是其对内超越了自己作为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的管理权限,在没有得到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的情况下,对外签订了担保合同。但是就对外代表权而言,无论法定代表人对内是否得到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的授权,对外一定还是由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签订合同,对外代表权的主体并没有发生变化。
(二)“法定代表制”下对外代表权并不能被限制
德国公司法上的代表人制度与我国个人法定代表人制度有较大不同。根据《有限责任公司法》及《股份法》,其实行的是“集体代表制+意定代表制”相结合的方式,即原则上有限责任公司由公司的经理(Geschäftsführer),股份有限公司由董事会(Vorstand)对外代表公司,在没有经理或董事会的情况下,有限责任公司则由股东(Gesellschafter),股份有限公司由监事会(Aufsichtsrat)对外代表公司;如果存在多位经理或多位董事时,由经理层或董事会集体对外代表公司,但是法律授权公司章程可以对代表人予以另行规定。
由于公司章程对代表人有权作出特别规定,因此就可能会出现各种差异化的代表人主体以及代表权范围,为了保障交易安全和稳定,德国公司法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规定可以限制代表权,但不得对抗第三人(未限定为“善意”第三人),而对股份有限公司则明确规定禁止限制其代表权。正因如此,德国法上通说认为,代表人的代表权逻辑上只能被“滥用”(Missbrauch),而不能被“超越”(Überschreitung)。
我国实行的是个人法定代表人制度,《民法典》和《公司法》对于法定代表人的权限和能够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主体均已作出明确规定,代表人的对外代表权也已经被法定了,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章程能够限制是只能是其对内的管理权而非对外的代表权。换言之,《民法典》中所谓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进行限制,其实是对身为法定代表人的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的对内管理权进行限制,而并非是就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对外代表权进行限制。
(三)与《合同法》第五十条比较
《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表述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超越权限”表述虽然笼统,但“权限”既可以指对外的代表权,也可以指对内的管理权。至于超越对内管理权的情况下,“代表行为”是否有效,可以理解为是超越对内管理权对代表权法律效力的影响。虽然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合同法》第五十条通常也是在代表权的层面上理解,但其表述仍然是规范的,而《民法总则》《民法典》所称的“代表权”,应该是对概念的一种不准确使用,实际是将代表权与管理权相混同了。
二
超越内部管理权的法律效果
——第三人是否负有调查义务?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担任着公司内部的管理职位,如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虽然其对外的代表权无法限制,但对内的管理权确实是可以限制的。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完全可以在不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就特定事项限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的内部管理权限,《公司法》第十六条关于对外担保的限制就是最典型的一种情形。问题在于,这种限制的对外法律效力如何把握?
德国通说认为,如果代表人在超越内部管理权的情况下对外代表公司实施法律行为,构成对代表权的滥用,并对由此给公司造成损害负有赔偿责任。对外的法律效力,根据《德国民法典》第242条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取决于第三方是否明知代表人存在滥用的行为。单从这一点看,如果将《民法典》中的“代表权”理解为“管理权”,似乎与德国公司法没有太大区别。
但是,由于将对外“代表权”与对内“管理权”混同,我国民法及公司法上对于法定代表人超越内部管理权的分析路径是将其理解为对外也“无权代表”,因此除非第三人有理由相信法定代表人没有超越代表权限(表见代表),否则就不构成善意;而德国的分析路径是对内构成越权,但对外是滥用代表权而非无权代表,因此,除非有证据证明第三人明知代表人滥用其代表权,否则就构成善意。由此导致了一个重要的差异:第三人是否负有对法定代表人超越对内管理权的调查义务。
德国法学界及司法实务中均一致认为,第三人对于代表人是否对内超越管理权不负有调查义务(keine Prüfungspflicht)。因为对内管理权是公司内部事务,没有理由要求第三人对此承担主动调查的义务,否则禁止限制代表权的核心立法目的——保障交易安全将事实上落空。因此,除非有证据证明第三人已经明知代表人对内越权,否则就应当认可第三人的善意。
对之相对应的是,《九民纪要》第18条明确规定了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中第三人的调查义务,只是基于是否是关联担保第三人的相应调查义务程度有所差异,并明确第三人承担的形式审查义务。但到了《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不再按照是否构成关联担保而区分第三人的调查义务,而且删去了“形式审查”的表述,而是一律要求债权人需要进行“合理审查”,第三人的调查义务事实上被进一步强化。
如果说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权限制是《公司法》的明确规定,对第三人施加相对严格一些的调查义务还有一定合理性,那么对于其他非法定管理权的限制是否也要准用这一判断标准就更加值得讨论了。如果对于非法定的限制也对第三人施加如此严苛的调查义务,其对整个市场交易安全的影响显而易见。应该说,对外代表权和对内管理权的概念混同是这一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
三
区分代表权与管理权
对公司行政责任承担的影响
除了民事责任以外 ,区分代表权与管理权对于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行政责任的承担也会产生影响。在许多行政法律规范中都有类似规定,即在公司违法的同时,对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要予以处罚。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否当然构成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其实,在区分代表权与管理权的前提下,这个问题本身就不能成立。由于法定代表人本身就是公司作为法人的对外代表,其承担的不是个人责任,因此不存在公司作为法人已经被处罚的情况下还要再对法定代表人个人再予处罚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内在担任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的过程中,是否构成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而这完全取决于具体案件中其在内部决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和个案证据而定。